咸涩的海水顺着衣领往下淌,我趴在礁石上咳嗽着,看着被浪打走的救生艇残骸。手表显示现在是下午3点17分,而我的喉咙已经像着了火——这是我在荒岛醒来的第一个小时。
摸着发烫的沙滩,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生存专家约翰·怀斯曼在《野外生存手册》里说过,人没有食物能活三周,没有水只能撑三天。我决定按这个优先级行动。
| 水源类型 | 日获取量 | 风险提示 |
| 椰子水 | 约500ml/个 | 过量饮用可能腹泻 |
| 树叶露水 | 100-200ml/晨 | 需过滤杂质 |
退潮时的礁石区成了我的天然冰箱。记得用尖树枝撬生蚝时,突然窜出的招潮蟹吓了我一跳——后来它成了我的蛋白质补给。
当我在棕榈树下发现带齿痕的果核时,后颈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这不是度假海岛,那些在树丛里沙沙作响的生物,可能正把我当猎物观察。
我用三天时间建起临时营地:
某夜被兽嚎惊醒时,我握紧自制的鱼叉长矛(用帐篷杆和瑞士军刀改造),才发现手心全是冷汗。那些绿幽幽的眼睛在十米外晃了半小时才离开。
第5天上午,我听到直升机轰鸣声。连滚带爬冲到沙滩时,只看到天边的白点——后来才想起那天是周末,可能是观光直升机。
参照《美军生存手册》的方法,我收集了六种引火材料:干椰绒、松脂块、朽木屑,甚至从相机里拆出电池和钢丝棉做了应急点火器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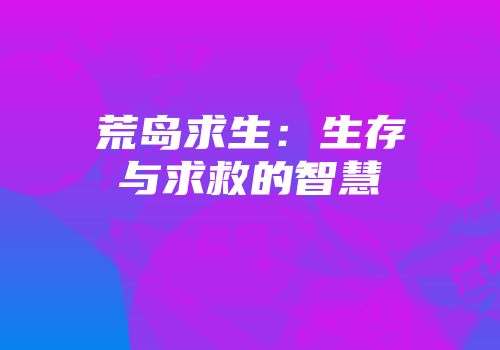
真正要命的是午夜惊涛拍岸时的心跳声,是发现淡水洼里有蛇蜕时的犹豫,是计算救援概率时的自我欺骗。我对着录音笔说话保持理智,用碳化的树枝在岩壁上画正字。
第11天下午,我在调试自制的棕榈叶滤水器时,突然听到东南方传来三短三长三短的哨音。手抖得差点打翻珍贵的淡水,抓起反光板就往山顶狂奔...
夕阳把海面染成琥珀色的时候,我看到救生艇的轮廓逐渐清晰。把最后半片压缩饼干塞进裤袋,我开始拆卸营地的预警装置——那些空罐头在风中叮当作响,像是在演奏荒岛版的送别曲。